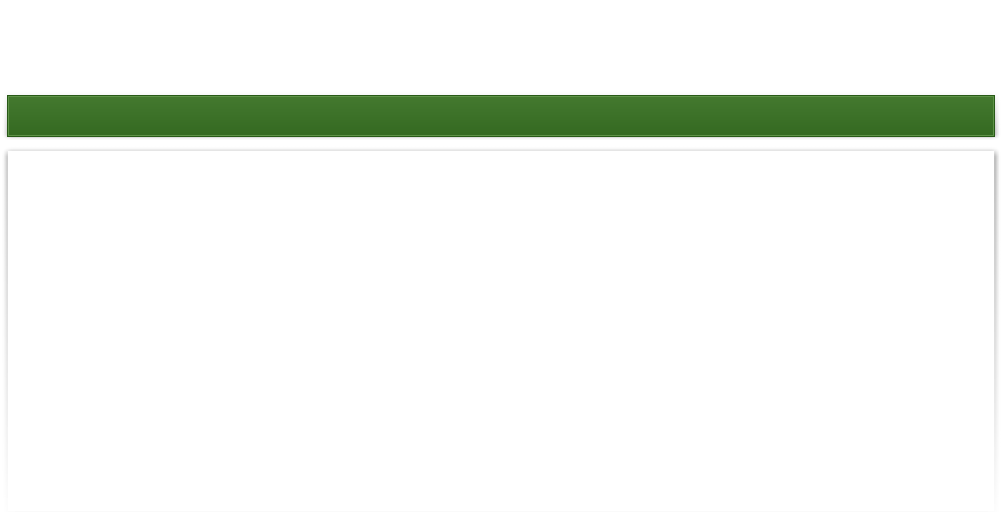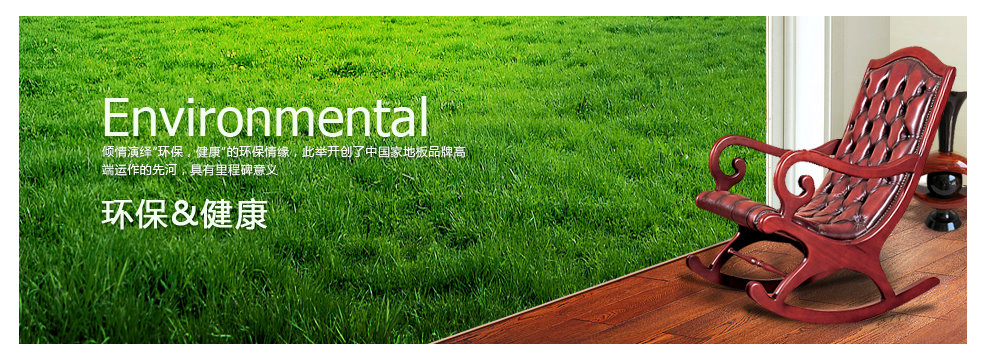车子每颠簸一下,我的心就跟着晃一晃。后备箱里装着给父母买的冬虫夏草和进口按摩仪,身上却穿着起球的旧毛衣。
堂哥朱炎彬去年盖了三层小楼,在家族群里发了整整十八张照片。表姐叶雅静的女儿考上民办大学,她挨家挨户收红包时说这是“教育投资”。
老张家的小超市扩了门面,招牌换成了红底金字。王婶家的院墙砌高了一截,顶上插着碎玻璃碴。
“俊远?”朱炎彬站起身,围着车子走半圈,手指在车门上抹了一把灰,“你这是……跑运输了?”
他打量着我的穿着——褪色的牛仔裤,袖口磨出毛边的夹克,还有脚上那双沾着泥的旧运动鞋。
“正常,做生意哪有稳赚的。”他拍拍我肩膀,力道有些重,“回来就好,踏实过日子。”
衣柜顶上,父母的合影还是十年前拍的。照片里他们头发乌黑,笑容里有种对未来的笃定。
“住多久都行。”父亲终于修好锄头,站起身,“西屋给你收拾出来了,被褥都是新的。”
朱炎彬家的三层小楼立在村东头最显眼的位置,罗马柱,琉璃瓦,阳台上摆着几盆蔫了的杜鹃花。
“包了点小工程。”他在真皮沙发上坐下,翘起腿,“去年给镇上修了两公里路,赚了这个数。”
“你当初要是留在县里,现在起码是科长了。”他说,“非要跑去南方创什么业。”
“别客气呀,都是自家人。”她在我旁边坐下,香水味有些浓,“听说你生意受挫了?哎哟,当初我们就劝你稳当点……”
“跟姐还客气什么。”她压低声音,“昨天我看见你往二婶枕头下塞东西,是银行卡吧?里头还有钱?”
“你堂哥那人,嘴上不说,心里其实挺替你可惜的。”她说,“当年你考上大学,他逢人就夸徐家出人才。”
“现在嘛……”她话锋一转,“村里人说话难听,你别往心里去。什么‘凤凰变土鸡’之类的,都是闲的。”
到家时,母亲正在腌咸菜。大缸里铺满青菜,她赤脚踩在上面,一下一下,用力均匀。
“俊远现在这样,你们也该想想以后。”叶雅静声音不小,“他三十多了,没成家,事业也没了,总不能一直靠你们养老。”
“姐是为你好。”她走到我面前,“我给你介绍个对象?镇上有家超市的闺女,虽然腿有点毛病,但人老实,嫁妆也给得多。”
“我说孩子的事,自己决定。”父亲刮着鱼鳞,动作熟练,“周支书说,村里缺年轻干部,你要愿意,他能推荐。”
月光如水,洒在老旧的门板上。门板上我小时候刻的身高线还在,一道道,从低到高。
朱家的院子里摆了三张大圆桌,桌上堆着瓜子花生和橘子。孩子们追逐打闹,大人们三五成群聊天。
菜陆续上桌:整鸡、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炖肘子,还有几个时蔬。酒是本地烧酒,用塑料壶装着。
四姑接话:“我早说,虚拟的东西靠不住。你看你堂哥,修路盖房,实实在在。”
表妹徐莉姿坐在邻桌,默默往这边看了一眼。她比我小四岁,在县小学当老师,文文静静的。
朱炎彬老婆端着酒杯过来:“俊远,嫂子敬你一杯。生意失败不可怕,怕的是没志气。以后有什么需要,跟你哥说。”
酒过三巡,大伯说起正事:“老太太还在医院,一天一千多。之前的钱用得差不多了,各家再凑点。”
奶奶躺在三人间的中间床位,身上插着管子。她瘦了很多,脸颊凹陷,手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。
徐莉姿去打开水,我靠在墙上,看着窗外的住院部花园。几个病人在晒太阳,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。
“医药费是个问题。”他说,“光这几天就花了小两万。大伯的意思是,如果后面要用贵价药,各家可能还得加钱。”
我想起来了。七岁那年,我在村口池塘玩水,差点淹死。是奶奶用竹竿把我捞上来的。
我没走,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,忧心忡忡的家属,还有轮床上推进推出的病人。
傍晚时分,奶奶醒了会儿,喝了点水。她看着我和父亲,忽然说:“我柜子里……有个铁盒子……给俊远……”
许久,他说:“你七岁那年,差点淹死。救上来后,我第一反应不是生气,是后怕。”
“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干工程,说看在我的面子上,给你安排个监工的活。”父亲的声音很平静,“一个月三千,包吃住。”
手机震动,是合伙人发来的消息:“徐总,深圳那个项目签了,首付款已到账。”
朱炎彬坐在堂屋里,手里端着一杯热茶。他今天穿得很正式,西装裤,皮鞋擦得锃亮。
我低头看去。确实是我的字迹,写着:“今借到朱炎彬人民币叁万元整,用于创业启动资金,两年内归还。”
“投资?”他笑了笑,“俊远,投资是要看项目的。你现在项目失败了,我这钱总不能打水漂吧?”
“连本带利。”他早有准备,“五年了,按民间借贷的规矩,怎么也得翻个倍。但咱们是兄弟,我给你算良心价:八万。”
“我知道你困难。”朱炎彬身体前倾,压低声音,“所以我想了个办法。你把县里那套小公寓抵押给我,这债就算了了。”
“别装傻。”他眼神变得锐利,“去年我听人说,你在县城滨江花园买了套房,八十多平。虽然现在房价跌了,但抵八万绰绰有余。”
我确实在滨江花园有套房,全款买的,当时花了六十五万。这件事我谁都没告诉。
“这你别管。”他靠回椅背,“怎么样?把房本给我,咱们两清。不然的话……”
他顿了顿:“我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到时候全村都知道你徐俊远欠债不还,你爸妈脸上也无光。”
“二婶,亲兄弟明算账。”朱炎彬不为所动,“三万元不是小数目,我也有家有口。”
“二婶,二叔。”她笑盈盈地打招呼,把一袋苹果放在桌上,“自家树上摘的,甜。”
“俊远也在啊。”她在我对面坐下,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,翻开,“今天来,是有点账要跟你对对。”
“这些年,你爸妈身体不好,去医院都是我陪着。”她开始按计算器,“2019年,二婶胆囊炎住院,我陪了三天,误工费一天两百,三天六百。”
“2020年,二叔摔伤腿,我每天送饭,送了半个月。人工费一天一百五,十五天两千二百五。”
“去年秋收,你家两亩稻子,我让老公开拖拉机帮你家收的。市场价一亩三百,两亩六百。”
“还有平时买药代付的钱,一共八百四。给二婶买的羽绒服,五百六。二叔生日我包的五百红包……”
“二婶,那是我客气。”叶雅静合上笔记本,“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俊远生意失败,你们家以后用钱的地方多,我也得为自己打算。”
“哦对了,”她又想起什么,“还有五年前你创业,我借你的两万块。你说半年还,这都五年了。”
“利息我就不多要了,算你三万。”她重新计算,“加上刚才的五千三百五,一共三万五千三百五十元。零头我给你抹了,三万五。”
“二叔,不是我不讲情面。”叶雅静叹气,“我家强强明年要上初中了,想送去县里读,择校费就得五万。我也是没办法。”
她笑了笑:“那我只能天天来家里坐了。你也知道,姐这张嘴,在村里说点什么,传得很快。”
下一篇:悦心健康涨212%成交额250亿元近5日主力净流入-192803万